
组织卖淫罪类罪辩护思路探析
文/ 王子逸
前言
组织卖淫罪是《刑法》第六章中相对的重罪。第六章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中,组织类罪名共有12个,其中,在不区分情节严重程度的前提下,按量刑起点大降序排列,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7年(众所周知涉黑犯罪有其特殊性),组织越狱罪与组织卖淫罪在同一档,均为5年以上,非法组织卖血罪、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为5年以下,其余罪名量刑起点均在2到3年。比较非法组织卖血与组织卖淫行为,二者均包含传播传染病的抽象危险,而组织卖淫罪的量刑较非法组织卖血罪却提高了一个档,且组织卖淫行为,一旦构成情节严重的(如“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”或“卖淫人员累计10人以上的”),刑期会直接提档到10年以上。实践中,稍具规模的组织卖淫团伙基本都有10人以上的卖淫人员规模,在无减轻情节的情况下,被控以该罪名的嫌疑人无疑会“牢底坐穿”,此情况下,轻罪辩护尤为必要。
根据《刑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,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均可以容纳“招募卖淫人员”的行为特征,而容留、介绍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表现又有一定的相似性,这无疑为变更罪名留下了极大辩护空间。一旦被控罪名由组织卖淫罪变更为前述二罪之一,量刑起点便相应降到5年以下。
本文试以组织卖淫罪罪名切入,重点探讨组织卖淫罪的类罪辩护思路。
一、无罪辩点
(一)辩点1 非进入式性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制的卖淫——何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
参考案例:任某某组织卖淫不起诉案 黑密检一部刑不诉〔2021〕Z16号
案例要旨:二次补充侦查后,检方仍认为“‘推油’(手淫)项目是否属于刑法范畴卖淫”证据不足,依法不起诉。
何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,理论界、实务界素有争议。依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法官周峰、党建军、陆建红、杨华《<涉卖淫类案件解释>理解与适用》一文的观点,口交、肛交、性交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,三者都是一方生殖器进入另一方的体内,均为进入式的性行为,此三种方式均可引起性病的传播,故肛交、口交应当列为卖淫的方式;同时,因刑法没法明确规定手淫等非进入式的性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“卖淫”,应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,对相关行为不宜入罪。
具体到本案,公安审查起诉认定:任某某组织按摩师从事的卖淫方式为“推油”(手淫),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“手淫”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活动,故作出不起诉决定。这正体现了这种观点。
(二)辩点2 单纯场所投资人(未参与经营)客观上没有管理或控制卖淫活动,且主观不知道场所内存在卖淫行为。
参考案例:龚某丙组织卖淫不起诉案 深龙华检刑不诉〔2020〕Z219号
案例要旨: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不起诉人龚某丙主观上明知会所有提供“口交”服务及客观上有参与会所控制经营管理的行为,也不足以认罪,依法对龚某不起诉。
当卖淫活动发生在洗浴中心等场所时,该场所除了卖淫活动外,往往还存在合法经营的服务(如洗浴、足疗等),该类场所的投资者(只投资未实际负责经营)在投资入股时可能不清楚该场所内存在卖淫活动,甚至有的是在该投资人投资后,在投资人不知情的前提下,出于某些原因场所(如场所效益不好、技师私下卖淫等)增加了“色情服务”。
按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115集《指导案例1267号席登松等组织卖淫案——组织卖淫罪的“组织”要件及情节严重程度如何认定》一文的观点,投资者只要明知实际经营者、管理控制者所进行的是组织卖淫活动,即使没有直接参与经营,没有直接对卖淫活动进行管理控制,其投资行为也应认定为组织卖淫行为的组成部分,因离开了投资者的投资,组织卖淫的规模会受到影响,甚至是否有经济实力实施组织卖淫行为都成问题。由此,如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投资人对该场所内存在卖淫活动知情的,则不宜认定为组织卖淫罪。原因在于,虽然客观上投资人的投资为卖淫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,然按“主客观相一致”的原则,此种情况下,投资人主观上没有参与组织卖淫活动的意愿,缺少犯罪故意。如果投资人清楚卖淫活动的存在,主观上可能对卖淫活动持反对态度,甚至会“撤股”乃至报案,不能仅凭投资行为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。
二、轻罪辩点
(一)协助组织卖淫罪
辩点 组织卖淫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罪行为的区别
参考案例:李某甲、李某乙协助组织卖淫案 (2015)粤高法刑一终字第287号
裁判要旨:李某乙在卖淫活动组织者的安排下,负责管理卖淫妇女的上班秩序及技师房的卫生工作,还负责从酒店的财务部领取卖淫用品卖给卖淫妇女,并每月向卖淫妇女收取30元卫生费,其行为依法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。
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状为“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、运送人员或有其他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”,根据最高院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下称“《涉卖淫案件解释》”)第4条,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、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、打手、管账人等的,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,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。一般而言,担任保镖、打手、管账人的行为表现与组织卖淫活动的组织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,较容易区分;然而,根据《涉卖淫案件解释》第1条规定,组织卖淫罪的行为特征表现“招募、雇佣、纠集手段,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”。因此,“管理和控制他人卖淫”无疑是区分“此罪和彼罪”的关键,笔者认为,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有二:
第一,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只涉及了组织卖淫活动的部分流程,而非贯穿全流程。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表现为招募、运送的,行为人对整个组织卖淫活动的参与一般“到此为止”,没有参与对组织卖淫活动的日常管理中(如制定卖淫服务价格、管理卖淫人员打卡上下班、分配收入等)。事实上,部分协助组织卖淫人员的行为不只服务于单一的卖淫团伙,有时同时服务多个卖淫团伙(如同时为多个卖淫团伙招募、运送人员),这种情况下,虽客观上其行为为卖淫活动提供了支持,主观上其也积极参加了组织卖淫活动,但此类行为仅属于为卖淫团伙的组织卖淫活动“配套”,行为人的“协助”地位亦更为显著,与组织卖淫行为贯穿卖淫活动整个始终的特征有明显区别。
第二,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落脚点在于“管理”和“控制”,该行为突出表现为对卖淫活动的日常管理,行为人通过制定一系列人、财、物管理规则,使其与卖淫人员形成的一种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”(如管理卖淫人员上下班打卡、制定服务项目内容、价格等)。这主要是为了保证卖淫活动在组织者管控下开展,保持卖淫活动的稳定经营,同时防范嫖客与卖淫人员之间产生纠纷、有关部门检查等,以最终实现其获利目的。为此,组织者往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、精力,或雇佣安排专人负责;反观协助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,该类行为只涉及到组织卖淫活动的“边缘地带”,仅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了帮助,而对于将卖淫组织及卖淫活动的具体运作一般在所不问,也没有参与对卖淫人员的指挥、管理和控制。
*值得注意的是,组织卖淫罪从犯≠协助组织卖淫罪。
根据《刑法》、《涉卖淫案件司法解释》规定,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有自己单独的行为特征,不能机械地认为“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一律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”。质言之,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一罪名,的确将部分组织卖淫罪的从犯正犯化,但并未将组织卖淫罪的全部从犯正犯化。参考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120集《指导案例第1309号胡杨等协助组织卖淫案——如何区分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》一文的观点,胡杨受雇于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后,担任该场所的经理,直接对该场所的卖淫活动进行经营和管理,其充当了整个卖淫活动的具体实施者,其行为本质上属于管理和控制卖淫人员的行为,而不是实施充当保镖、打手、管账人等角色,也不是帮助招募、运送人员等处于协助地位的行为;胡杨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,因胡杨终究只是受雇于、听命于卖淫团伙的幕后老板,主观恶性、社会危害性相对幕后老板余永洪要小,可以认定其为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地位。
在提出辩护观点时,要正确理解该二个罪名的区别与联系,如某人的行为确属组织卖淫行为时,辩护人要审查行为人是否受雇于人或听命于人,在“组织卖淫罪从犯”的框架内为其争取辩护空间,一旦被认定为从犯并减轻处罚的,量刑同样可能到5年以下;而非提出“离谱”的辩护观点,强行为其作罪名之辩。
(二)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辩点1 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行为人存在组织行为的,认定为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参考案例:徐敏等涉嫌组织卖淫案 (2020)赣0191刑初168号
裁判要旨:(案发时现场查获了四名女子)在案证据足以证明,案发别墅内存在卖淫活动,徐敏等人实施了招嫖、容留、介绍卖淫活动的行为,构成容留、介绍卖淫罪。
该案卖淫人员已达4人,卖淫场所营业期间(2个月左右)涉案账户总收款75万余元,,在案证据亦未能证明徐敏等人制定具体人、财、物管理规则,管理或控制卖淫人员、卖淫活动,且收款方系苏州某公司银行账户,在案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人的具体非法获利金额;第一次开庭结束后,检方向法院提交《变更起诉决定书》变更指控徐敏等3人构成容留、介绍卖淫罪。最终法院以容留、介绍卖淫罪判处徐敏有期徒刑2年,其余两人分别判处1年零3个月、1年。
前文已述,组织卖淫行为呈现出“管理或控制”的组织化特征,在个案证据未达到证明组织行为存在的证明标准时,就不宜认定为组织卖淫罪;由于卖淫活动客观发生,且行为人确实为之从事了招嫖、提供场所等行为的,应以容留、介绍卖淫罪定罪为宜。
辩点2 场所内卖淫人员不足3人,应认定为介绍卖淫
参考案例: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270号 何鹏燕等介绍卖淫案
根据《涉卖淫案件解释》第1条,要认定组织卖淫罪,卖淫人员须在3人以上。这里的3人应当理解为“同时管理、控制3人以上”,而非“累计管理、控制3人以上”。原因在于组织卖淫的危害性正在于组织性、规模性,在同一时段内,卖淫人员被组织、集中起来并达3人以上,卖淫活动在时、空间上较为密集,形成了“规模效应”,相校于容留、介绍卖淫行为(卖淫人员、活动较松散)社会危害性更大。如果理解为“累计3人以上”,则会不当扩大组织卖淫罪的打击面,导致“罪刑不相适应”。
具体而言,应当在个案中审慎审查在案发当日以及卖淫活动持续期间,是否有证据证明卖淫人员在“同一时段内达到3人以上”。只有被卖淫组织“管理或控制”的卖淫人员才算数,“今天来、明天走”,松散地从事了1次、2次卖淫活动的,应当予以剔除;“来了、走了、又回来了”的,只能计为1人。
三、罪轻辩点
(一)特定人员仅提供非进入式性行为的,人数、涉案金额相应剔除
前文已述,手淫等非进入式的性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,在此基础上,如果特定人员仅从事非进入式性行为的,当然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“卖淫人员”。相应地,在人数上、非法获利上均应予以剔除。
(二)审查是否存在重复计算卖淫人员的情况
同一卖淫人员在同一卖淫团伙“来了、走了、又回来了”的,只能计作一人,尤其要注意的是,这种情况下,卖淫人员的“工号”、“艺名”往往会变化,应综合审查全案证据,反复对照涉案人员笔录内容和卖淫场所、团伙的人员名单、服务流水单等,准确确定卖淫人员人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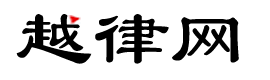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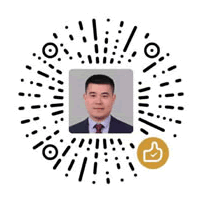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